游戏论|情感权力与爱情游戏:从《清宫计》到《盛世天下》
在《女王的游戏:盛世天下》(下文简称《盛世天下》)开场三分钟左右,玩家就被推入了一场毫无缓冲的宫斗困局。女主角武元照作为新入选的才人,随队进入内宫,此时,自幼相识并一同入宫的好友悄悄递来一支牡丹发簪作为赠礼,推辞间发簪意外坠地,恰好惊动了路过的贵妃。贵妃追问簪子的主人,游戏由此弹出第一个选项:自己、好友或是另一位秀女。

《盛世天下》关于簪子的选择
若玩家选择承认簪子属于自己所有,游戏会进一步给出三个细化的回应,但是无论后续如何回答,死亡结局都已注定,因为贵妃最爱牡丹,不容他人佩戴牡丹饰品。若选择“好友的”,所谓的挚友立刻反咬一口,声称是你意图嫁祸——她的“馈赠”原本就是一场要置你于死地的陷阱——结局则是你和好友双双殒命。只有将责任推向另一位秀女,才能苟且保命,而被指认者则代你而死。在五选一的困局中,大部分玩家须先死一死,才能找到唯一的生路。这是《盛世天下》给玩家立的“下马威”,也是它宣传时最醒目的卖点:“你能活几集?”

《盛世天下》官方宣传图
根据steam页面的介绍,《盛世天下》是一款“真人互动宫廷冒险游戏”,虽然游戏创造了一个颇为时髦的新词来给自己定位,但玩家们在2010年代流行的“宫斗游戏”中早有体验类似的风格。彼时,橙光平台的宫斗游戏也常以“多种死法”“步步惊心”等语汇来凸显游戏内容的紧张与刺激,并将各种稀奇死因作为游戏之吸引力的一部分。可以说,《盛世天下》是在真人影视的外壳下重复了这一传统。不过,问题也因此浮现,为什么十年之后,在宫斗题材的媒介形式和技术包装都已天翻地覆的今天,仍要依赖同样的卖点?在“互动影游”,或邓剑所说的“游戏剧”的新形态下,宫斗题材的叙事内核与机制逻辑发生了怎样的延续与改变?
换句话说,笔者想讨论的并不是《盛世天下》是否成功嫁接了影视与游戏,而是一个更抽象的问题——当宫斗叙事在不断变换的媒介形式中反复出现时,它所固守、暴露并放大的,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深层结构?
《清宫计》:橙光与宫斗的“姻缘”起始
谈到宫斗题材与游戏媒介的结合,不得不提及号称“首款宫斗游戏”的《清宫计》。《清宫计》是一款于2013年在橙光平台推出的文字冒险游戏(Adventure Game,下文简称AVG)。彼时的橙光,尚未成为如今玩家们耳熟能详的AVG“巨头”,根据创始人柳晓宇的说法,橙光平台最初试图通过对标“美少女游戏”(ギャルゲーム)吸引男性玩家。然而,我国监管政策限制了对该类游戏来说至关重要的亲密互动与视觉刺激,这一尝试注定难以为继。就在橙光陷入困境之际,《清宫计》的横空出世改变了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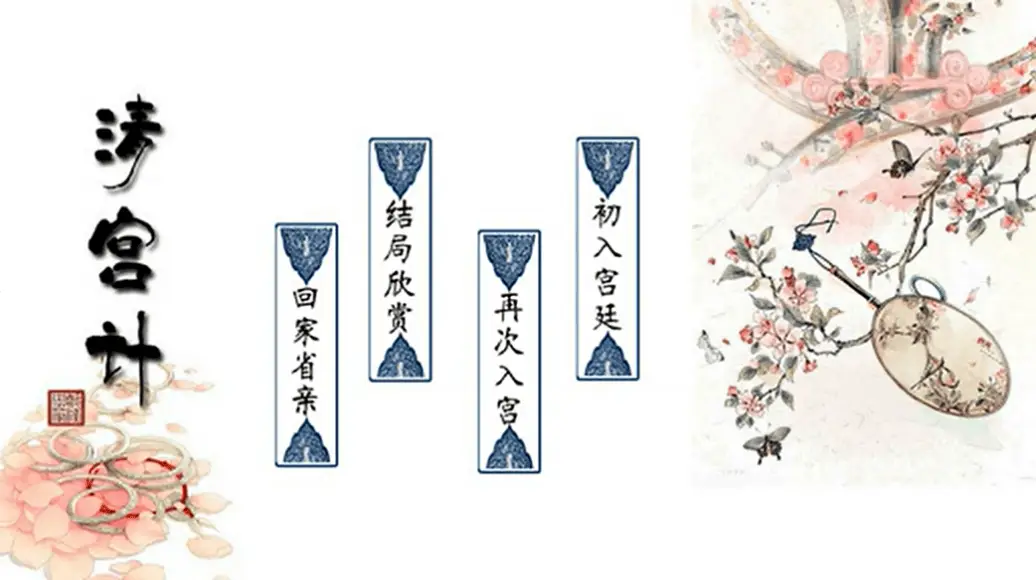
《清宫计》
2010年代,清宫剧在电视荧屏风头正盛。《步步惊心》《甄嬛传》等剧集不断刷新收视率,也培养了观众对后宫题材的高度兴趣。《清宫计》以清宫为背景,让玩家扮演官家小姐富察如雅参与后宫斗争之路,并与不同男性角色展开爱情故事。这些人物设定直接借鉴了当时热播清宫剧的形象,太医秦墨言显然来自《甄嬛传》中的太医温实初,怀亲王玄哲也几乎是果郡王允礼的翻版,宫斗桥段更是融合了多部影视剧的情节逻辑,甚至连立绘都直接使用了清宫剧人物。对于剧迷而言,《清宫计》提供的恰是一个化身“剧中人”的机会。
《清宫计》确立了宫斗游戏的基本叙事逻辑——生存与惩罚。玩家化身宫斗新手逐渐卷入权力斗争,在游戏过程中需要不停做出选择,每一次选择都是生死攸关的节点:承认一桩小错,可能被打入冷宫;与某位妃嫔结盟,或许立即招致他人嫉恨;甚至一次偶然的迟疑,都可能触发死亡结局。

《清宫计》使用清宫剧中人物做立绘
这种叙事逻辑完全改变了“选择”在AVG中的意义。AVG作为以文字故事为核心展开的游戏类型,需要通过选项和底层数值的配合,让玩家控制文本行进的方向。比如在美少女游戏里,玩家要以选择行为提升与角色之间的好感度,最终进入该角色的故事线。但是在宫斗游戏里,真正“有效”的,即可以导向不同故事线的选项十分有限,大部分时候玩家面对的都是“选错即死”的局面,玩家始终如履薄冰,时刻面临生存压力。从这个角度来讲,宫斗游戏竟然和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逃杀游戏”有诸多相似之处,正如邓剑所说,它构建了一个处在永恒紧急状态的“游戏集中营”。
可以说,《清宫计》的成功得益于它巧妙地嫁接了三股力量:清宫剧的流行,女性受众的情感想象,以及游戏媒介给予玩家的控制感。恋爱内容是《清宫计》的重要一环,但它并不完全是恋爱游戏,因为其最初的重点在“计”而非“情”。玩家在后宫中求生,更多体验的是“生死抉择”带来的紧张与刺激。
随着橙光平台女性用户对情感叙事的需求日益增长,《清宫计》也进行了数次更新。开发者逐步加入更多男性主角,并补充了大量恋爱剧情。这样一来,游戏逐渐演化为“宫斗+恋爱”的混合体。与此同时,宫斗类游戏也在橙光平台持续繁荣,《后宫三千人》《进击的宫斗》《深宫未归人》等经典作品不断出现,系统和机制越来越丰富,数值系统也更加复杂,玩家不仅要进行选择,还需要养成主角的“心机”“好感”“势力”等数值。
但需注意的是,无论情感内容和养成机制如何膨胀,都未能取代宫斗游戏里权力带来的特殊体验。所谓权力,不仅是帝王的意志或妃嫔之间的争宠,更是一种无处不在的制度性约束:礼仪规训、等级秩序、禁忌规则、人情世故,共同具象为游戏系统,构成了后宫运作的基本逻辑。玩家在游戏中所面对的数值,本质上就是权力的不同面向。心机意味着自我约束与他人算计的能力,势力代表着在等级秩序中的生存筹码,而好感则是一种情感化的权力资源。换句话说,宫斗游戏的所有叙事转折与机制运算,归根结底都在模拟权力的流动与再分配。而“选错即死”的叙事逻辑,则是最直观的“故事权力化”的形式,这种单向度的即时反馈,将复杂的权力逻辑完全简化,轻易就塑造出了一个残酷的权力场。
可以说,宫斗题材在橙光平台的兴起,既是偶然,也是必然。偶然在于《清宫计》恰逢清宫剧热潮,将观众的观看兴趣无缝转化为游戏体验;必然在于,它精准契合了女性受众日益增长的“权力想象”。这种想象并非关于社会或政治制度,而是以家庭伦理和亲密关系为舞台展开,既是权力斗争,也是情感纠葛。因此,橙光与宫斗之间的“姻缘”才得以逐渐固化为平台的经典品类。十余年后的现在,宫斗不再只是借助清宫剧余温的副产品,而成为橙光的支柱题材之一。
橙光+短剧:《盛世天下》的网络文学内核
《盛世天下》改编自2015年在橙光平台发布的同名游戏,其故事框架、人物设定、选项设置均与原作差别不大。游戏以武则天的历史故事为蓝本,背景设定在贞观末年,玩家扮演的武元照的命运与历史紧密相连。游戏开篇,她以才人身份入宫,先后扳倒韦贵妃、杨淑妃,又卷入魏王与晋王的废太子之争,与高阳公主成为好友,却因未能救下高阳心爱之人而反目。官方目前仅推出“媚娘篇”,以唐太宗逝世、武元照被迫入感业寺为尼收尾,之后的“女帝篇”将继续讲述她如何走向权力巅峰,并与两位男性角色展开更为复杂的情感纠葛。

武元照被迫入长安感业寺为尼
表面看来,《盛世天下》就是把原作故事整体“升级”成了真人影视。选项驱动的剧情分支、“选错即死”等机制都被保留下来,它的“橙光基因”毋庸置疑。但《盛世天下》的另一重血统却来自网络短剧。仅从人员配置上看,《盛世天下》的短剧属性就格外突出。剧中使用了许多短剧演员,导演知竹更是活跃于短剧行业,曾执导《长公主在上》《东栏雪》等热剧。这一背景决定了游戏在视觉与叙事上的短剧化倾向:快节奏的情节推进,MV式故事渲染,大量怼脸特写,追求的是短时间内的情绪抓取。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23年底掀起互动影游热潮的《完蛋!我被美女包围了》(以下简称《完蛋》)。如果把《盛世天下》比喻为“完蛋热”的延续——这从商业逻辑上是成立的,毕竟它们同样依赖影视化手段,在多平台同步上线,以制造话题效应。但若放在类型发展的脉络中,两者却几乎南辕北辙。《完蛋》及其衍生的“完蛋类”作品,直接继承了美少女游戏的传统,与具有橙光和短剧血统的《盛世天下》差别极大。这种差异在影视化风格上尤为明显。《完蛋》模仿游戏的第一人称视角,镜头就是玩家/主角的眼睛,男主从不出现在画面中,玩家的体验是“沉浸式恋爱”。相比之下,《盛世天下》采用的是短剧拍法,女主角武元照频繁出现在屏幕中央,她的表情、动作乃至服饰都构成了主要的观看对象。换句话说,玩家的体验在很大程度上是“观看武元照”,而不是“成为武元照”。这里的差异,正好凸显了两类互动影游背后的不同逻辑:《完蛋》依赖恋爱游戏的情感递进,目标是攻略并确认关系;《盛世天下》则继承宫斗游戏的生存逻辑,核心是危机与权力。也正因为如此,《盛世天下》并不能看作是“完蛋类”的“女性向版本”。

《盛世天下》中的武元照镜头







